从2013年的“中国经济升级版”、2014年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到今年的“互联网+”概念,中国经济在崭新的起跑点上已经找到了“新的动力源”和“成长升级”的具体方案。虽然,进入2015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依然在相对稳定中试探中长期底部,但是“触底反弹”却已经距离我们不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历了2013-2014年以来最严重“行业困难”情形的国内大屏行业,应如何摆正自己的历史观,制定怎样的企业中期战略就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等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大屏企业极可能面临:1、继续在此前两年的困境中徘徊,2、亦失去对未来新增长机遇的把握能力,进而使得企业的发展遭遇存亡考验。
以上这个问题,也是本文中笔者将着重解答的问题。
大环境:什么是互联网+
对于大多数人,互联网+还是一个陌生概念,没有形成产业性的统一认识。甚至,少部分人依然将互联网+认为就是电商,就是上网卖东西——这样的认识必然不能深刻了解“互联网+”之中的巨大产业机遇。
科学正确的认识“互联网+”概念,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之上。而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解释,更多的媒体导向是“增速降低”。这样的解读同样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含义应当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再”全球化的秩序重构。
其中,全球经济背景将是一个关键的核心因素:
全球经济的大背景是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改变了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其中,两个标志性的解雇是:第一,欧洲实现了欧盟级别的财政和货币权利的集中,这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德国亦在二战后首次真正回归到了欧洲政治经济的全方位领导地位;第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再工业化过程,尤其是2013年德国提出工业4.0和智能工业革命技术爆发以来,08年到2013年期间,全球初级制造业向越南、菲律宾、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戛然而止”,同时,所谓金砖国家中除了已经实现全面工业化的中国外,其他国家的发展都遭遇了一定困难(资源和重工业领先缺乏轻工业的俄国面临乌克兰危机后的“制裁”考验;巴西和印度经历了货币贬值和大起大落的GDP考验;南非甚至在2015年4月份发生了一定的骚乱事件)。
此外,金融危机的另四个副产物是:1.“印钞”战争,美元、日元、欧元先后进入量化宽松政策,预期未来人民币也具有在一定背景下量化宽松的可能性,其中尤其以日元的量化宽松对于救活其出口型企业和高负债财政作用最直接;2.欧洲,如英法、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全球经济领头羊如美国先后出台了“有史以来水分最大的会计准则和GDP统计方法”,这种强行拔高GDP的行为,充分说明了少数国家在政府债务问题上的严重性,甚至不得已不用“掩耳盗铃”的方法来拖延时间;3.美国全球权力的收缩和调整,带来局部权力真空,这与其政治软实力的频繁使用一起,构成了东欧、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地区一些国家动荡的核心原因;4.全球经济低迷,使得强人政府更为盛行,例如今年初希腊大选为代表的欧洲保守主义和右派的登场,美国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四月份财政部长楼继伟对美国的批评),世界银行改革的乏力,印度和印尼新领袖的当选等。
以上这些宏观国际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外部条件:1.出口经济增长遭遇瓶颈,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皆是如此;2.中国工业经济的竞争由主要担心向成本洼地回流,变成了应对工业4.0背景下,美国为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挑战;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国际动荡也加剧了海外投资权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4.中国经济的全球话语权谈判陷入僵局,不得不启动亚投行等新工具;5.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从军事和同盟手段为主,向挑动中国经济关键邻邦国内稳定和直接贸易战为主转变(如泛亚铁路沿线的政治困境和TPP)。

当然,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来自于内部,其主要表现是:1.从企业到政府端的“升级欲望”,经济向高端发展的战略至少已经实施了10年以上,从上届政府的振兴装备产业开始,或者从上上届政府的振兴国防产业开始,这个周期是漫长且空前具有共识的;2.新技术的颠覆作用,主要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智能工业机器人技术导致传统产业的巨大变革(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核心原因:“人力成本劣势因素”将逐渐消失,这为美国在资金、技术、资源、内需市场、高水平技术工人等有利条件下,实施再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成为阻碍初级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最核心力量);3.解决区域发展平衡问题和国内公平问题的挑战,这一问题的起始时间也超过了十年,典型的转折点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京津翼一体化政策;4.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挑战,上文提到金融危机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就要求我们经济走出去的时候要有新手段(丝路基金等)、更多资源投入(如安全资源,亚丁湾巡航)、更大的诚意(如4月份习大大访问巴铁);5.国内部分资源过度消耗的瓶颈,例如低端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依靠互联网+和工业机器人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的结构性资源缺陷(中小企业融资要更多的靠金融改革解决)、环境容量资源的消耗(如雾霾问题)、区域公共资源瓶颈(如北京堵车问题,要靠京津翼一体化解决)、大尺度下的公平问题(如今年开始的高考困难农村地区另招政策)、政府资源效率的问题(简政放权、治理庸官懒官和反腐败)——总之,资源瓶颈涵盖了自然资源到社会资源的广阔范畴 ,这些都需要经济升级来解决;6,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问题,如何避免更多的摩擦、建立更多的共识需要智慧和耐心。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不是简单的“增幅降低”:实际上,即便印度号称超越我们的GDP增速,2014年其能贡献的全球增量不过是1400亿美元,而中国确是7000亿美元——因此,中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种结构性的挑战。其核心是“经济升级”的问题:包括矿产和环境资源消耗方式、政府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再生与高效运作、金融和产业资源的整合与走出去的一路一带战略等等,每一项都指向“升级”二字。或者说,经济升级既是中国目前所谓新常态的出发点,也是经济新常态的过程和目标。
而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关键节点,或者说命门在哪里呢?自然不是外部的全球经济环境问题,如美国的遏制政策;也不是廉价劳动力资源逐步枯竭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新技术的问题”。这个所谓的“新技术”核心是指“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升级和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政府、金融、对外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这就是李克强总理2015年两会提出的“互联网+”。
综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机和工业4.0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面,经济升级则是打开这个基本面的锁头,而这把锁头的钥匙就是“互联网+”。理顺了这个逻辑关系,也就认识了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的内在含义。
互联网+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传统产业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1.新技术手段带来更高的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企业经济的边际成本——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甚至说,企业边际成本正在向零端运动,典型表现是电商的成长;2.互联网带来了新的社会公平机制,包括信息获取的平等(微博微信)、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参与的平等(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反腐)、以及社会治理和管理的革命(智慧城市、公民个人信息系统等);3.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提供了工业4.0和终身学习计划的最低成本平台,它将改造我们的制造、消费和学习过程。
以上三个方面的互联网+作用是目前看得到,正在发生的“力量”。除此之外,互联网+提供的想象力空间有多大,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在中国经济升级的大趋势下,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的过程中,已经蕴藏了无数成长性财富机遇,这早已是社会共识。对此,大屏产业也需要未雨绸缪,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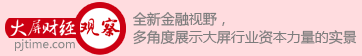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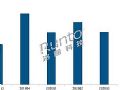





 WAP手机版
WAP手机版 建议反馈
建议反馈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PjTime
PjTime